代孕“流水线”:“制造”孩子,就像一场赌博
从小到大,我经历过孩童间以玩具、食品互换的以物易物,也深入参与着现代社会围绕金钱展开的商品交易。不过,这些交易对象基本都是特定“物品”或者“服务”,我从不会想到有一天有人将孩子作为特殊交易物,明码实价。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孩子很多时候会为一个家庭带来一种微妙的平衡。在隐秘的地下代孕市场,通过试管婴儿技术筛选,合成胚胎后移植到另一个女人子宫里孕育,诞生的孩子体内有一半可能一辈子都见不到的女人的基因。
健康的孩子落地、交接,代孕机构和代孕妈妈可以拿到最后一笔大头费用,客户也可以如愿花钱抱得想要的孩子。
尽管代孕技术日趋成熟,但这仍然像一场赌博,各方都明白有失败的可能。如果孩子是“不健康的”,这场交易就失败了,就像一个被制造出的“瑕疵品”,孩子的命运会是什么呢?
2020年8月底,澎湃质量报告栏目历时20余天,通过暗访调查,推出《疫情下的代孕市场》专题策划,受到舆论关注。作为采写者,我想从选题思路、突破角度、背后细节等方面回溯这个特别的故事。
寻找代孕者
新闻线索来自给澎湃新闻爆料的一位网友。他反映,在国内某款主打同性交友的APP内,散布有为“男同性恋群体代孕”的小广告。
代孕其实不是一个新话题,但一位业内人士向我们介绍,疫情对这个行业“影响挺大”,这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观察角度。
主编和团队沟通,希望做到三点:求全、求新,有画面。
一是要求全。此前一些媒体也关注过代孕,但大部分都是从代孕妈妈、卵妹、中介单一方面呈现,探访、口述及引用偏多。我们要呈现出代孕这个地下产业的全链条,单家探访或者链条上一方说法难以呈现整个业态,信息的真伪度也会打折扣。
此外,回归问题根本,需要从监管和立法两个维度,医学伦理和法律秩序两个层面做出建设性的探讨。
二是要求新。“代孕市场”背后是一个隐秘的行业生态,生态就有各个环节,我们想探究疫情是如何影响整个生态链的。
而在成稿时,我们侧重呈现增量,如突出同性群体如何代孕、代孕公司如何“蒙混过关”分娩孩子,“假结婚”给孩子上户内容,淡化卖卵女孩的市场行情,如何取卵等此前为人熟知的内容。
三是要有画面。调查内容配有暗访的画面,更为直观。这增加了选题调查难度,危险性也会提升。
起初,我们的身份不断在“捐卵者”、“收卵者”、“代孕需求者”几个角色间变换。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些角色在代孕链条中的故事,我们以“代孕”为关键词在贴吧、微博、知乎、豆瓣等平台上寻找线索,发现一些人会将自己的代孕和捐卵经历发布。我们主动私信,表明自己同样也有类似需求,希望能进一步聊聊,找到了不少人。
我们也以“代孕需求者”的身份发布信息。当时有一些人加我们,但大多数都是代孕中介,他们同样潜伏在这些平台,不仅毫不忌讳地发布代孕信息,还会在涉及代孕的个人帖子下留言。
一番接触后,我们选择实地探访四地的四家代孕机构,身份便是“想要孩子的男同性恋”。
选择这个身份,一是考虑到有代孕需求的同性恋者在代孕客户中的比例逐年上升。二是实地探访要与代孕中介近距离接触,但我们记者年纪不大,不太像不孕不育,需要代孕的夫妻,更不像“失独”的群体。
暗访的较量
暗访前,我们在着装打扮、言行举止方面做了一番研磨训练,主要是让代孕中介不产生疑心。此外,我们还需要一个有说服力的职业身份——毕竟代孕套餐费用高达几十万元。
4天时间,我们以“证券从业者、律师、教师、传媒从业者”四种社会身份周旋于四家中介公司之间,刻意向对方透露所在行业的信息,让对方疑心渐渐消除。
几家代孕公司面对我们这个“金主”,急于想签下单子,并获取到我们无意有意流露出来的潜在客户群体,这一行同行竞争激烈。
我们利用这一点,试探出代孕公司负责人的底线,“逼迫”对方不断让步,带我们去探访了孕妈基地、合作医院,并吐露了行业内幕。
因为是暗访,需要现场随机应变,控制整体“节奏”。不能让对方感到咄咄逼人、意图过于明显,也不能放过每一个追问的点。
在一家代孕公司,我们不断逼问对方往年做了多少代孕案例,有无不健康婴儿的诞生,一时让“会谈”气氛压抑,对方对于敏感信息不愿意多说。我们便转换话题,聊起轻松些的,之后再有意带出问题。
另外,暗访中,拍摄的原始素材时长超过5小时,很多时候直接是面对面拍摄,设备最近时离对方不到半米。在一个封闭空间,为了转移对方注意力,本不抽烟的我们也通过发烟、抽烟的动作,以此调整拍摄角度。
有一次,因为拍摄的设备电量过低,突然闪了一下蓝灯,被对方发现。“你的表还会发光?”“喔,电子表,带着玩,跟您的表比不值一提。”我们当时赶忙打圆场,惊出一身冷汗。所幸,对方警惕性不强,没有深究。
当然,不是所有信息都适合暗访,哪些信息需要,值不值得冒险,都要权衡。
一家代孕公司的人带我们看完孕妈基地后,在车后座,他兴奋度高,突然讲起来他们如何和医院、医生合作分成,我们赶紧打开设备,记录下这个重要信息。
孕妈和卖卵女孩
找到合适的采访对象其实很麻烦,尤其在代孕行业,很多人背着亲友,不愿意多说。学会“借力”、“广撒网”是团队采用的方法。
首先是“借力”。我们以真心想要代孕,想要先了解为由,向代孕公司负责人索取代孕的客户和部分代孕妈妈的联系方式,对方考虑到我们是“诚心”,便欣然提供了几位。
此外,我们也被中介公司带去了代孕妈妈基地,顺道采访了两位代孕妈妈。在一处居民楼上,一名来自云南文山和一名来自四川西昌的代孕妈妈被安置在此,一人即将分娩,另有一人刚怀上几个月。交谈中,我们才得知,其中一人25岁,一人27岁,一人丈夫知道自己做代孕,一人家里人都不知情。
为了22至25万元的佣金,她们远离家乡,怀上别人的孩子,没有人比他们更想要孩子顺利分娩,因为可以拿到最多的一笔佣金。“我们那里很多人做这个啊。”临走时,西昌的代孕妈妈说。
“广撒网”则是借助互联网,团队分工在网上各个角落搜集一些代孕客户、代孕妈妈和卖卵女孩联系方式,分头联系。
特别说明的是,在代孕客户方面,主要有不孕者、失独者、同性恋者三大群体。此前媒体更多聚焦不孕者,我们结合暗访接触的实际情况,决定另辟蹊径,寻找“同性代孕群体”,呈现出他们的故事。
通过在社交平台检索,我们加入了一个“山东形婚群”,里面的群成员大多是同性恋者,每天都会有一些同性恋者在里面发布“形婚需求”,其中就会提到是否需要孩子,是否考虑代孕。
我们联系到几位想要孩子的同性恋者,其中有两位男同性恋者已经通过代孕有了孩子。一位男同性恋者认为代孕是与代孕者互惠互利的事,“我有需求,而她们正好也有这个意愿”。在豆瓣,我们还发现了一位患艾滋病后通过代孕有了孩子的男同,他在豆瓣上记录从得知自己的性取向到患艾滋病再到选择代孕有了孩子的过程。和其他同性恋者不一样的是,在代孕之前,他必须要通过洗精子这个环节,而为了父母,他选择形婚,和一位他并不爱的女子结婚,这位女子同时也扮演着供卵者的角色。
我们发现他们选择代孕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传宗接代”,给父母一个交代,二是喜欢孩子。这些内容有的我们考虑再三,没有放在文章中。
在这个链条上,作为供卵者的一方又有怎样的故事呢?我们在豆瓣、知乎、微博、QQ等社交平台上以“捐卵”、“卵子”、“后悔”、“教训”等作为关键词检索,试图找到愿意分享捐卵经历的亲历者亦或是受害者。以同样有捐卵需要的在校女大学生的身份,我们私信了20余位自称有过捐卵经历的网友,但鲜有人回复。
最终采访到一名捐卵女孩,她是在学姐的介绍下联系上了代孕机构,以3万元的“补贴”出售了自己的卵子。她并不后悔自己做的选择,只是带些内疚地说,这或许是很多年轻人都会经历的。
另一位“卵妹”是经中介机构介绍的,她对采访显露出极大的兴趣。与前一位受访者不同,她认为捐卵这一行为不仅有经济激励,也是对社会和他人的贡献。比照海外代孕合法化的情形,她认为国内卵子库的缺失暴露出传统观念的束缚,而以个人行为去推动试管技术的应用、医疗制度的完善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
代孕过程中,卖卵女孩需要向代孕机构提供一系列个人信息,除长相、年龄、身高、体重、血型、视力等基本生理状况外,还要求进行学历认证、户籍证明。
在这个过程中,中介所承诺的隐私保护、正式签约前不会泄露个人资料只是一纸空谈。这些卖卵女孩的资料被买卖卵子的中介打包后向所有的代孕机构公开,它们被放置在资源池中,明码标价供代孕机构里的客户挑选。
代孕往何处去
目前,国内对商业代孕持禁止态度。
现实是,放开二孩后很多人发现无法再生育,还有一些失去独生子女的群体,他们想要孩子的需求很急迫。国内现有的辅助生殖中心周期长、排队人数多,“一票难求”,很多人因此转向商业代孕。
另一方面,商业代孕在利益的驱使下,乱象丛生。我们接触发现,一些代孕生产的孩子患病后会遭到遗弃,代孕妈妈也可能会终生不育甚至造成身体不可逆伤害,一些卖卵女孩取卵后得了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OHSS)。此外,“蒙混过关”分娩、用欺骗手段给孩子落户都是在突破法律的底线,代孕孩子的抚养和监护权纠纷,最近几年频频出现。
在摸清行业生态后,还需厘清它的产生背景、国内环境、国际社会监管态度,最终回归问题根本:代孕该何去何从?
我们查询大量公开报道、学者文献资料,将欧洲、美国及前几年比较热的“东南亚”各国监管层对代孕的监管和立法信息整理,将国内“社会不允,法律不禁”的现状呈现,辅之采访国内辅助生殖中心负责人和关注此现象的法律从业者、医生,完成了一次具有撬动意义的探讨。
正如几位专家所言,代孕现象禁绝不了,甚至规模越来越大,背后是现实需求的集中凸显,靠堵能解决问题吗?在采访中,我们也感到,代孕群体的诉求不能在现行体制中得到满足,他们转而寻求这个出口,仅“公序良俗”一词恐怕很难阻绝。
如何在现有医疗制度中构建替代体系?能否合法化?这需要我们的监管层和立法层去思考。
来源:澎湃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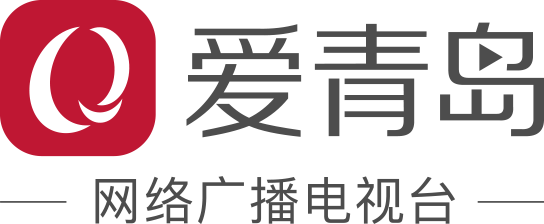

 公安备案号:37020202000242
公安备案号:37020202000242